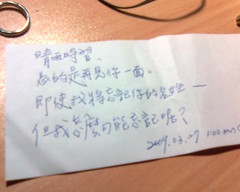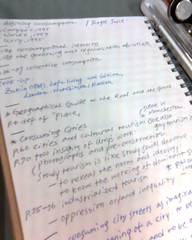消費社會:在「物」的天空底下
「消費,是捍衛文化以及使之成形的主要戰場。」
--Douglas & Isherwood(1979: 57)
這是一個消費社會。我們走進店鋪,走出店鋪。百貨公司,商場,量販店。我們拿起各種商品,反覆揀選然後帶走它們,或者將它們放回原來的地方。商品呼喊著滿溢出來。我們選擇,今天要到哪一間咖啡館,喝哪兒進口的咖啡。今天要吃甚麼,我今天穿的樣子適合走進那間餐廳嗎?這是公平交易咖啡豆,或者不是。我們穿上新衣,或許將舊的丟棄。生活似乎充滿選擇充滿變化。惟一不變的原則是,我們掏出錢包,帶走或得到我們所渴望的。無論我們需不需要。消費是現代社會主要(但並非唯一)的文化場域。而且,由於資本主義不斷地開發消費工具(means of consumption),消費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更是愈加地活躍(劉維公,2001)。
「消費」可簡單地定義為基於求生存、便利或舒適之生活目的,使用或消耗商品財務。Mark Jayne(2006, 4-5)梳整消費的操作型定義,指出消費是:
「人們透過商品或服務的選擇、購買、使用、再使用與丟棄的過
程(Campbell, 1995),表達自我認同、標誌個人所屬社會團體
的特質、展現秀異,與確保社會參與的實踐體系(Warde, 1997:
304)。消費成為人們對建構、經驗、詮釋、使用空間與地方意
義的重要方式(Urry, 1995)。」
整體而言,正因為消費是「社會關係與論述的複雜領域,其焦點為商品的銷售、購買、與使用(Mansvelt, 2005: 7),」消費、生產與社會的關係,從來就不是單向的。它不應該只是單純的物質/精神的二元對立。消費可以同時是異化與救贖,可以同時區分差異並促進同質化(differentiate and homogenize),「消費」的一致就是它的矛盾。它儼然已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的大敘事(grand narratives)。消費地點的多元化、商品與勞物交換的體系日益成熟、消費財與資訊流動的擴張,凡此種種讓「消費」日漸取代了「生產(與生產體系的矛盾)」,而成為後/現代社會的主要趨力(Corrigan, 1997;轉引自Mansvelt, 2005: 2)。人類的消費活動已不只是被市場供需與價格所決定,也不是完全基於心理的需求與滿足、甚至刺激與反應模式來行動 ,而是透過消費行動維繫自我與生活場域的持續建構(劉維公,2001);Robert Sack(1992)即以織品(loom)比喻消費世界,以商品的性質、意義、與社會關係等抽象認知為線,而人們在消費商品時便將這些元素與個人經驗混合,編成具備現實與幻想、本真與抽象意義的「織品」。
Jean Baudrillard(1990; 1996; 1998)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切入,將「消費」的意涵從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領域解放出來,直指符號意義的過剩生產,乃是當代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社會情境。Baudrillard主張人們慾求的、看見的、消費的乃是「符號」而非「商品」(signs rather than commodities),他的消費文化論述致力於證成「要被消費,物品本身必須成為符號」的命題,消費的目的是消費符號,消費商品的生產,則是在創造符號的價值,由是,消費行為在結構上受制於符號(constraint of signification);而在社會-經濟-政治層面受制於生產(constraint of production)。在消費社會中,商品的符號價值,已經遠遠超出它本身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。在Baudrillard 的論述中,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創造了社會階級的貧富之別,也不是商人告訴消費者「你不滿足」,所有這些都是被「消費體系」本身所定義的,關鍵在個人,而非集體。消費體系正是透過區分「消費行為」的高下貴賤,來維繫它本身的運作。消費就是消費社會的惟一原則。George Simmel(1978;轉引自Mansvelt, 2005: 11)即悲觀地認為,物質與非物質「商品」客體文化(objective culture)的快速成長,以及人類對於物質文化的充分掌握,將導致社會文化的悲劇;Alan Tomlinson(1989: 13)也曾犀利地指出,「主張『商品都是我以勞力換取的工資主動購買的』,因此『選擇商品』的自由是『自我』的自由,那麼對那些沒有能力消費的人們而言,難道他們就不配擁有自由了嗎?」Baudrillard對於消費文化的未來有著與Simmel類似的看法,亦悲觀地認為「消費者」的主體性將在消費當中消解、甚至被符號產製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擬象困縛,終於導致整個社會與其生產的符號共同內爆而終結。在「物」的天空底下,一切原始的、現代性的邊界都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曖昧不清的新的邊界。然而,這種說法將個人的主體性放至過低的層次,並無法充分解釋在發達資本主義體系當中,消費者如何主動地介入商品/符號意義的解讀、確認、與再建構。
隨美學化、品牌化與標準化的生產過程,繽紛多元的商品乍看之下提供了差異的選項,實際上,卻正對原先物理上、地理上具有不同特性的消費場域進行著去差異化(de-differentiation)的工作,而這種情況,也隨著全球化去領域化(de-territorialization)進程的發展而更加鮮明(Mansvelt, 2001)。有學者便認為,隨著全球同質化對原先具備差異特色的地方進行再殖民的工作,在地性的財貨將被源自西方、或承載了西方文化符號的商品給取代,地方性的文化差異性與多樣性因此遭到侵蝕(Howes, 1996;轉引自Mansvelt, 2001)。但「概括論之」的敘事不可能全然無誤地適用所有地方,若因此而預言一個跨地域的超全球市場即將形成,則不免是低估了個人與社群評估、使用商品,並對之進行價值選取與符號意義的內化過程中介入的程度。克里歐化(Creolization)的典範即指出,「人」同時作為文化的生產者與接收者,乃是主動、具創造力、並具備歷史經驗性的角色,在接收來自西方的文化與商品符號過程中,能夠選擇性地挪用文化元素,創造出適用於地方脈絡的價值意義(Howes, 1996: 2;轉引自Mansvelt)。另一方面,Homi Bhabha(1994;轉引自汪琪、葉月瑜,2007)則認為,在後殖民的文化語境中,混雜(hybridization)開啟了西方/中心/殖民者、地方/邊陲/被殖民者雙方以外的第三空間,消除了中心與邊陲的界線、與其他二元對立式的文化傳遞模式,在這個空間中,文化的組成份子得以相互轉換,是對帝國權勢進行鬥爭的場域,試圖去除帝國主義論中「被殖民者僅能被動地接受影響」的線性邏輯;Pieterse(1995;轉引自汪琪、葉月瑜,2007)更認為,「混雜」動搖了長久以來先驗地被視為本質性的、國族性的、種族主義式的文化概念,透過混雜,有助於觀察者在「想像上」跨越國家、民族、階級等等概念中僵固的二元分立。
現代人的社會生活被消費商品所密集地籠罩著,固然,文化中介者(cultural intermediaries)為產品創造了符號價值,提供當代資本主義重要的獲利基礎,但在商品行銷的過程中,消費者無論是否被迫,也都不曾真正停止與商品所傳遞、所承載的符號意義進行互動。超全球化也好、克里歐化或混雜也罷,這些想像世界圖像如何被商品、符號與文化的加速傳遞給重新塑造的方式,都必然存有獨特的同質過程經驗與特殊主義(Mansvelt, 2005: 172),生產與消費網絡對文化產生的影響,不光是內容改變了甚麼,而是透過各種「交換形式」的變遷,人們得以用更多的方式與他人溝通彼此的差異,並進一步將自身納入整個符號交換的體系。
Alan Tomlinson(1989: 29)指出,若將商品的社會意涵分作功能-整體生活風格-獨特生活風格-品味鑑賞等四個層級,其重要性的排列,隨現代性/後現代性的生成,逐漸從階層狀轉而破碎(from hierarchy to fragmentation),由尖頂的金字塔形,逐漸轉為整體生活風格與獨特生活風格引領風騷的紡錘狀。劉維公(2001)認為,正因為文化符號與經濟體系的相互交纏、膨脹,個體在消費歷程中要滿足的已不是經濟面與心理面的需求,而是透過消費行為來實踐生活美學,建構生活風格,一方面培養出固定的消費/行動模式,同時也透過生活風格與其他個人或團體的差異,來展現個人的秀異(distinction)特質。Featherstone(2007:65-69)稱此現象為「日常生活的美學化(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)」,隨著文化工業興起,富設計感的消費商品擴散,並使得大量文化「符號」廣泛地進入大眾生活的同時,藝術、美學感受、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邊界便遭到消解。
物/人關係的改變,也影響了消費者認知自我在社會關係中的「位置」。Bernard Cova(1997: 299-300)指出,在後現代狀況下,商品勞務的迅速流動讓消費行為成為個人體驗世界的重要管道。商品圍繞個人的程度越強,個人就越不需要其他穩固的社會連結,個人的社會連結越罕,則依賴商品來建構生活情境的狀況也就越發根深柢固,一種自我中心的後現代個人主義(ego-centrated postmodern individualism)於焉成形。然而社會性並未真正被捨棄。相對於個人主義往個體中心匯聚的認同形式,個人透過消費文化建構、投射於「物」的認同,在資訊流通更加通達的狀況下,把隱而不顯、面目朦朧而有著同類別「商品」認同的個人,凝聚為後現代部落(postmodern tribe)。有別於現代性意義論述下的「社會」結構,後現代部落不再仰賴血緣、地域、宗教與儀式等元素連結個人,而是透過資訊與情感的共享、新的道德信仰、或者--更重要的,類似的消費實踐形式--來完成身份與社會結構/部落的想像(Bauman, 1992: 157-158)。後現代部落具備流動的、沒有涇渭分明的疆界、不一定屬地(of space/ place)的特質,而貫串其中的正是「符號儀式」的反覆操演與交換,Mike Featherstone(2007)便指出,這是消費文化中商品作為拜物儀式的回歸,商品/消費行為承載了情緒和社群共想的感受結構,讓後現代個人得以重新整合儀式、商品、與生活美學,並對之進行操演與超越。但究其根基,符號才是後現代部落真正的核心命題,儀式不是。
消費主義隨資本主義全球化而擴散,一方面為跨越地域的同志文化帶來互動的可能,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更多具象、可見的商品符號,取代原先顯得曖昧不明的「地方社群性」,成為同志群體認同的重要元素。對地方文化造成了「必須接受霸權文化輸入」的壓力──當身體、服飾、配件,乃至於呼應種種「展演」的行為已成為了消費文化的戰場,東南亞、加勒比海、中南美洲等後殖民國家內部的區域同志文化,也就在這波媒介/商品全球化的浪潮中,所呈現出各種對男性身體形象的再現、虛擬、以及想像,而受到了深刻的影響(Altman, 1996: 85-87)。固然,在行銷學家(Haslop, Hill, and Schmidt, 1998)的眼中,同志族群的消費能力是一個人人皆欲搶食的大餅,但同志社群的地域關係往往並不固定、也沒有其可明顯辨識的歷史脈絡,這種「單靠著性別認同形塑」的社群,消費行為的屬性往往隨著情境與偏好而有很大程度的差異;但這也正是同志社群所具備的利基,正因為「重點不是我們是誰,而是我們做了甚麼,」消費者若將自身投射於某個後現代部落,則社群也將成為鼓勵消費者以風格與消費行動表達自我、展現認同的重要趨力(Fugate, 1993: 48;轉引自Haslop等人, 1998)。
然而單單將個人視為投入消費行為以獲得差異、進而建構自我的消費者主體觀,又未免失之扁平。即使個人透過購物與消費「表演」其社會認同,背後的身體實踐、空間性與歸屬感(relatedness)等自我反身的過程,也都在消費決策與商品的使用中扮演重要角色(Mansvelt, 2001: 99)。Lunt & Livingstone(1992:24)即主張,消費行為的心理歷程讓人們得以建構認同、形構人際關係、並且透過「物」來框架並區認事件的意義。
Miller(1997: 45, 轉引自Mansvelt, 2005:121)也認為,消費行為不僅顯示了消費者所欲展現的「社會關係」,更進一步表現了消費者如何表示「存在」的認知模式。不可否認的,從裡到外,「身體」是個人社會體驗的重要場所,誠如Mike Featherstone(1982: 1)所言:「在消費文化中,身體是快樂和表現自我的載體。苦行般的身體勞作帶來的不再是對靈魂的救贖或更健康的身體,而是得到改善的外表和更具市場潛力的自我。」消費牽涉了自我與他者邊界的形成,而在人們的互動過程中,保持外表、形象、營造良好印象,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著力之處(Goffman, 1972;轉引自Featherstone, 1982);借用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來談,人們在與周遭他人的互動經驗與意見交換當中,透過「他人的眼睛」來看見自己,經過各種不同階段、層面、來源的鏡像反射,反覆修訂、辯證、體現、定位自我,並進一步落實在消費與身體的工作。Featherstone(1982)認為,傳統的價值和道德觀念受到市場的影響,逐漸淡薄散去,人們越來越依賴「消費」來展現個人休閒、嗜好與品味,社會經驗的實踐與購買行動的關係,因此更加密不可分。到「某個地方消費」代表著某種特定層級的外表與品味,不完美的身體被視為不正常的身體,人們必須透過更加嚴格的身體管訓與控制,來展現自身的社會資本--當然,也是透過「消費」來改變。在後續的論述中,Featherstone更進一步指出,布爾喬亞階級在日常生活美學化的社會歷程當中著墨最多,「文明社會」對自然「低等」的身體(包括體態胖瘦、髮式、衣著、氣味、汗水、甚至是情緒反應)進行各種規訓與控制的手段,可說是透過種類益發多元的消費商品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(Featherstone, 2007: 79)。
消費改變個人、改變了社會關係,也深刻地改變了當代城市空間的樣貌。隨重工業佔經濟整體比重下降,符號經濟拆解了福特主義(Fordism)講究效率與功能掛帥的指導原則,城市中,製造與設計產業不再惟「工業」為尊,而開始轉向生產「供縉紳階級(gentrifiers)使用、維持特定生活風格」的產品(Zukin, 1998: 825-828)。城市不再是單單圍繞著「生產結構」而建造的空間,功能取向的空間營造策略不再受到特別的偏愛,標準化的建築與商品已成昨日黃花,取而代之的是富含設計感與各種文化符號的混雜結果。城市已不只是商品的集散地,而是符號產出的地點--那正是「符號消費」所打造的後現代城市外觀(Jayne, 2006: 58)。而在微觀的空間層次上,當代都會的地景,向是被從不停止的社會行動所「產製」出來,不同的空間使用行為--而非功能--定義了空間在社會意涵上的差異。這導致了城市空間的碎形現象(fragmentation),正如同Michel Foucault在〈Of Other Space〉中提出的「異托邦(heterotopias)」概念,城市的空間被分割,被設計成為滿足社會理想分工體制的樣貌,當空間功能被行動細緻地劃分到極致,即成為烏托邦的實現之處。所有的真實空間,同時呈現在城市當中,相互競爭、甚至獲得社會意義上的翻轉,形成了一些處在「其他場所外部的」局部空間(Rushbrook, 2002: 185)。作為空間與社會意義的橋接處所,消費行為提供了個人據以經驗「城市生活」的強力面向。消費空間作為個人進出的實體空間,也是生產社會意義的場所,Robert Sack(1992)曾針對百貨公司、量販商場、主題樂園等各種提供大眾消費功能的場景進行分析,主張這類地景串接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現實,讓大眾透過消費與購買行為滿足幻想,由是,人們「越消費就越能表現自我(Sack, 1992: 153)」,但Sack主張「消費能克服後現代狀況中的異化與失向(disorientation)」的論點,卻也因為「消費本身便具備異化的特質」而備受質疑(如Warf, 1994;轉引自Mansvelt, 2005: 58)。
無論如何,Sack的論述點出一個長久在(生產的)政治經濟學中隱而不顯的重要論域:「消費」的政治性。商品與商業文化的研究,向來是挑戰消費/生產二元對立的重要領域(Mansvelt, 2005: 157),作為文化、生產、經濟、消費的交集之處,消費的空間政治實際上便包含了「人們在日常基礎上互動」的意義,而消費空間受到生產-消費鏈的影響,其配置成型的過程也必然隱含著權力運作的軌跡。消費行為跨越空間,便讓商品鍊與生產環境的互動過程得以跨越地域存在,也影響了不同地域的個體/社群。而知識在消費的空間政治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--消費者透過消費行動(買與不買、到哪裡買、如何買的決策歷程)來對生產-配送-消費的權力結構作出回應--就這個層次而言,「消費政治」的定義為「對日常生活條件的控制權力」,換言之,消費者對此政治結構的抵抗、服膺、或順從,正是透過其「消費能力」所能發揮的經濟效應,來展現其消費行為的主體性(Hartwick, 1999: 1183-1184)。由於同志空間乃是同志社群娛樂、社交、表達認同的重要社會空間,在一些針對同志空間進行的研究中,即發現同志社群透過集中挹注消費,來表現其對維繫同志村落存在的支持(Haslop等人,1998)。而「消費」本身亦成為空間中促動服務供應者、消費者、商品生產者互動的複雜過程,新的空間意義與風潮,從中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--即有論者主張,前往同志酒吧與俱樂部消費,可被視為一種「個人認同」的表現形式,而也同時是同志個體所浸淫其中的「次文化」本身(Haslop等人,1998)。